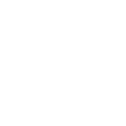中华自然国学不但古老、辉煌,而且新颖、充满时代的活力、价值连城。
1.一门时代呼唤的学问
中华自然国学是门综合性学问,它横跨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自然史学,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生成性、有机性、直觉性、人文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与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有关;与中国人尊重自然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都“生生不已”,视自然界为生命的孕育过程密切相关;与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内向性,擅长通过体验、直觉等内省性形式认识外部世界相关联。这些特性决定了中华自然国学对世界的认识,重综合而不是分析,偏重于整体而不是局部,偏重于直觉、灵感而不是逻辑、演绎。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重理性,轻感性;重分析、轻综合,到近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尔更是如此。随着工业社会发展而形成的近代科学,是分析型科学体系,具有明显的分析性、还原性、构造性、逻辑性、演绎性等特性。这与西方人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密切相关;与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切割和占有,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和整体,空间的本质则趋向分解和局部有关;也与西方人趋向于外向性思维,侧重有形的实体与物质构成,喜爱分析,在群体中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构成,具有分割性研究和讲究逻辑、演绎的传统相关。
东西方人的思维、文化颇有对称性的优势互补,东西方的科学体系亦有颇为对称性的优势互补,本应该取长补短,协同发展,这有利于西方,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东方和中国。但是在强权主义时代,西方独尊,他们绝不允许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强盛,绝不允许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有话语权。近几百年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分析型科学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资本社会的大繁荣和大发展,缔造了史前无例的工业文明,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分析型科学重视局部,忽略整体;重视结构,忽略功能;重视线性运动,忽视非线性运动;长于分析,短于综合。客观世界是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线性与非线性的统一,不但需要分析,而且还要综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分析型科学体系的不足愈来愈明显,愈来愈适应不了客观世界的发展与需要。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分析型科学强调征服自然,引发了人类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掠夺,恶化了大自然整体良性发展的环境,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全球性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等,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于是,整体性科学迅速地发展和崛起,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得到重视,富有整体性的、人文性的、天人合一论的中华自然国学开始复兴。可见,自然国学之新颖是新在当代综合科学时代之需。著者不提出这个概念,也会有其他人提出这个概念,这是时代潮流。
有人说自然国学就是科学技术史,没有必要另提一个新概念。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在研究内容上两者并不相同,自然国学比科学技术史宽广得多,它还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国历史自然学。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很不相同,科学技术史偏重于分析型研究、分科性研究,自然国学偏重于综合型研究、整体性研究。诚如宋正海教授所言,自然国学与科学技术史的不同,“正如中西医有区别那样,是整体论与还原论(或说整体论与分析论,著者注”的区别”。
事实也已说明两者是很不相同的,《自然国学丛书》已出版的有《孔子自然观初探》《庄子自然观》《邹衍自然观》《董仲舒自然观)《张载自然观)(苏轼自然现)《朱熹的自然研究》《王夫之的自然世界》《<周易>的科学理念》《<春秋>科学考》《<周礼>的自然生态观》《元气论,自然国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石》《太极系列,自然界的联系网络》等书,都不可能是科学技术史领域的研究和成果。
2.一门充满活力的学问
正因为自然国学是一门时代呼唤的学问,所以它充满活力。
20世纪50年代初,射电天文学研究兴起。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N.C.什克洛夫斯基,“向中国科学院请求研究中国的史书”,以“证实新星爆炸”。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席泽宗接受了此项研究任务。1955年,什克洛夫斯基看到席泽宗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超新星记录与射电源关系论证的论文,不但全文吸收采用,而且兴奋地说:“超时代的最新科学——无线电天文学(现称射电天文学)的成就,和伟大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记录联系起来了。”什克洛夫斯基还说,中国古人的观测记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纳入了“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宝库,我们贪婪地吸取史书里一行行的每一个字”。并称赞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人已经“是第一流的观测者”。
197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文中指出:距今500~3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冬季温度高2-5℃,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距今3000年中国气候有一系列冷暖波动,每个波动历时300-800年,年平场温度变化为0.5~1℃;等等。文章轰动中国和世界,被立即译成英、德、法、日和阿拉伯诸种文字。英国《自然》杂志称赞说:竺可桢论点“特别有说服力”,西方学者“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高兴”。此文的资料来自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记、日记、地方志等书籍,竺可桢从1925年开始收集,花费了47年。这篇论文开创了中国和世界历史气候学研究方向。
2001年初,中国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第一次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得最高奖的科学家是数学家吴文俊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吴文俊于20世纪50年代在拓扑学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导出“吴公式”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转向中国传统数学史研究。他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机械化思想、几何学代数化的方法应用到当代数学前沿——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研究,发明一种方法,被命名为“吴文俊消元法”,简称“吴方法”。自1975年后的几年中,此法成功地证明了600多个定理,1977年在平面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获得成功,1978年推广到微分几何,以后又推广到非欧几何、仿射几何等。1983年,中国留美学者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吴方法,并一鼓作气证明了500多个几何定理,轰动国际学术界。1990年以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发展到整个数学机械化的研究,取得超出预期目标的成果,并陆续应用到相关的理论物理研究、计算机科学和机器人机构学中,从而得到国家最高科技奖。吴文俊指出,“吴方法”是“我国自《九章算术》以迄宋元时期数学的直接继承”,并认为“继续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的机械化特色……建立机械化数学,则是本世纪(20世纪,著者注)以至可能绵亘整个21世纪才能大体趋于完善的事”,我们的目标是使“中国数学传统机械化思想的光芒,普照于整个数学的各个角落”。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蕾院士说:“最令吴先生自豪的是他‘第一个认识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真实价值’”,并以此开辟了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2015年12月10日,诺员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隆重举行,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登台领奖。屠呦呦及其团队以40多年前发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医学界也是中国科学界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最高奖项。该项研究始于1964年,1967年成立“523”科研组,屠呦呦1969年加入,并任科研组组长。该组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参加,前后参与人员共500多人。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重大流行性疾病,死亡率很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抗疟疾药物,如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员就已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仍没有找到理想的抗疟疾药。屠呦呦他们坚信依靠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定会找到理想的抗疟疾药,她另辟蹊径,从研究中国本草入手,翻阅大量古籍,收集、整理出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中国方药,又从中精选编辑成含有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一一进行实验。在经历190次失败后,居助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青蒿一握,以上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记载中得到灵感,提出用乙醚替代酒精,并低温提取,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第191号原料中提取的药物获得对疟原虫100%的抑制率,最终确认了青蒿的抗疟作用。然后,屠呦呦与有关同事为验证青蒿素有否毒性,不顾危险毅然在自己身上做试验。1978年通过鉴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非洲推荐该药,拯教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疾愈出院的患者高呼“中国神药”。青蒿素,为中医药,系中国原创,也是迄今中国唯一被世界公认的原创新药。获奖后,屠呦呦深有感触地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中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发现、挖掘和研究。”
3.一门价值连城的学问
自然国学的提出和复兴,无论是其实用价值还是理论价值都很大。从目前已看到的,著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有利于克服百余年国学研究的重大缺陷,建立全面国学观。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学”一词,百余年来国学研究的成果丰硕,涌现出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等大家,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北京大学国学五大家(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胡适、冯友兰),20世纪海外新儒学四大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励、徐复观),以及郭沫若、钱穆、季羡林、张岱年、饶宗颐等。然而,他们的研究领域都毫无例外地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早在90多年前,清华国学院主持人吴宓教授似觉察了这个问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在大力开展人文社会内容研究的同时,要研究国学中的自然知识,他说:“自然方面,如河川的变迁,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要专门之研究。”
季羡林、张岱年教授在晚年对此也似有觉察,他们极力支持我们对传统文化开展人文与科技综合性研究,同意担任宋正海、孙关龙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书的顾问。季羡林教授指出“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且于2007年提出开展大国学研究方向‘。张岱年教授专门出席了我们于1995年召开的“《天地生人丛书》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强调对传统文化要开展人文、科技的综合研究,提出“科学易”的研究是易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2001年又专门为我们题字“自然国学之光”。令人遗憾的是吴宓、季羡林、张岱年的真知灼见,均没有引起国学界的重视或足够重视。所以,百余年来的国学研究,存在着缺失自然国学这一重大缺陷。
也正因为这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自然国学”一词,不得不发表《自然国学宣言》,以指出国学还存在一个长期缺失的,与已有的人文社会国学同样古老、同样辉煌的自然国学。这样,从学科体系上和整体性上揭示了国学的基本构成和本质特征,有益于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研究国学,从根本上纠正百余年的国学片面观,实现国学认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可以说,自然国学概念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中国全面国学观开始建立。同时,自然国学概念的提出扩展了国学内容,有利于国学的综合研究,提升国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它表明国学中不是仅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体系,还有一个自然和科学技术的内容、体系。这样,不但理所当然地把“四大发明”“郑和七下西洋”“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都江堰”“大运河”“颐和园”“苏州园林”“历史灾异录记”和《考工记》《黄帝内经》《九章算术》《水经注》《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等纳入国学范畴,而且也理所当然地把整个中国传统思维(含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生态观、方法论等)、整个传统科学技术(含天学、地学、算学、农学、医学、技术工艺学等)、整个历史自然学(历史天文学、历史地质学、历史地貌学、历史气候学、历史水文学、历史植物学、历史动物学等)全部纳入国学范畴,使国学包含的内容极大地扩展、充实。这有利于克服以往国学研究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内容所造成的误区和死角,开拓整体性国学综合研究的新方向,亦大大地有利于国学更好、更全面地结合当今的实际(不仅是思想道德领域的实际,而且还包括自然、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实际)开展研究,真正地实现季羡林先生大国学研究的方向。这将有力地提升国学的地位和价值,特别是提升国学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创新中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有利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研究的深入,开辟一系列新研究领域,获取一系列崭新成果。用西方传入的近现代科学体系及其分析论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且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英国李约瑟的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又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应该继续进行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产生了许多盲点、死角导致了许多曲解、误识。而从自然国学体系及其整体论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成就,会产生一系列崭新的研究领域、崭新的研究课题,并有一系列的新发现。
例如上述竺可桢开创的历史气候学研究、吴文俊开创的机械化数学、屠呦呦团队发明的青蒿素药物。又如孙关龙发现《春秋》中首创系统的自然记录,尤其是系统的历史灾异记录,已成为当今全球气候变化、探索自然史和宇宙一些变化规律等不可或缺的史料,还首创“陨石”“地震”“山崩”等名词,发现《尔雅》是集先秦自然国学之作,是现知中国和世界最早的科学的知识分类著述。现代科学已发展到综合研究时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研究再也不能局限于西方的分科论体系和分析论研究方法。
第三,有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辟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获取一系列崭新成果。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尤其是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论研究,包括对诸子百家自然观等方面研究基本缺失,造成了一系列的曲解和误认。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向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说的天,基本上仍然是当时传统的宗教所说的天、帝或上帝,是宇宙最高的主宰”;孔子不但主张“自然界的事情是受上帝的命令支配的”,还认为“人的生死、贫富、贵贱,以及成功、失败,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即以研究诸子百家的自然观为重点,开拓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获取了一系列新成果,如《孔子自然观初论》等。刘长林的《中国象科学观》,开拓了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研究。相信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国学研究者肯定会在这方面贡献更多的成果。
第四,有利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道路。自然国学思路、体系、方法等与现在流行的西方科学技术的思路、体系、方法等,很不一样。自然国学具有崇尚生成论、讲究整体观和有机观、勤于观察、善于推类、重于应用等优点,西方近代科学则具有崇尚结构论、讲究局部观和分析观、勤于实验、擅长逻辑、重于效益等优点。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它们的结合会迸发出无限的创造性思维,前述的竺可桢、吴文俊、屠呦呦是如此,国外创立协同学的H.哈肯、耗散结构理论的I.普里高津、有机建筑论的F.L怀特等无不如此。
人们常说中国原始创新不够,那是近现代,是自然国学被泯灭的年代。在自然国学发展的古代,中国人富有创新精神,其技术、工艺的发明数量不但位列世界各国之首,而且超过古代世界各国技术和工艺发明之总和。事实证明,中华自然国学具有创新性思维。当代中国创新不够,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缺乏国学知识和思维,尤其是缺乏自然国学知识和思维。前些年笔者发表的《自然国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源泉》一文中即指出:自然国学能在观念上、理论上、方法上、史料上、技术基因上、灵感上等方面对当代科技创新发挥重大的启迪或实用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科学高度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系统学科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促使科学从简单科学时代进入复杂科学时代,从线性科学时代进入非线性科学时代,从分析型科学时代进入综合型科学时代。概括为一句话:从小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我国科技人员不能再故步自封,死守分科性体系、分析论方法,而置富具整体观、生态观、有机观的中国人自己的自然国学于不顾,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吃。试想,科学已从分析型为主的时代进入综合型为主的时代,从分科论为主的时代进入整体论为主的时代,我们的科技人员如果还仅有过去在学校中学到的分析型、分科论思维(顺便说一下,科学进入综合型为主、整体论为主的时代已有数十年,我们的教育却依然停留在分析型、分科论的时代,太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随时代前进,不注重学习综合型、整体论思维,怎么能跟上当今科学发展的步伐?怎么会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性思维?
中国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道路,也必须继承光大自然国学。众多事实已经证明,自然国学中的整体观、生成观、天人合一观、有机观、和谐观、元气说、阴阳说、中庸说、相生相克说、天地人“三才”说、道法自然说、厚德载物说、经络说、太极模型、象数论、有机建筑论、因地制宜论、因人制宜论,以及数学机械化法、生物除虫治虫法、医学以毒攻毒法等,至今仍有价值,甚至有时比现代科学的一些学说、观点更适合当前的交叉科学时代、综合科学时代,更能解决一些非线性问题、复杂性问题。亦已证明中国特有的地域广阔、数量巨大、类型多样、连续性好、较为可靠、系列又长的自然史料,至今仍有价值,且是世界上他国所不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自然史料。因此,只要重视自然国学,中国完全有条件加快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也完全有条件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道路。
——本文节选自学术集刊《自然国学评论》中《自然国学:一门新颖而古老的学问》一文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做陈列之用)
[责编:tdsr]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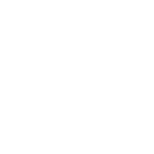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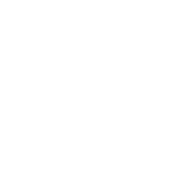
tdsrwz@163.com